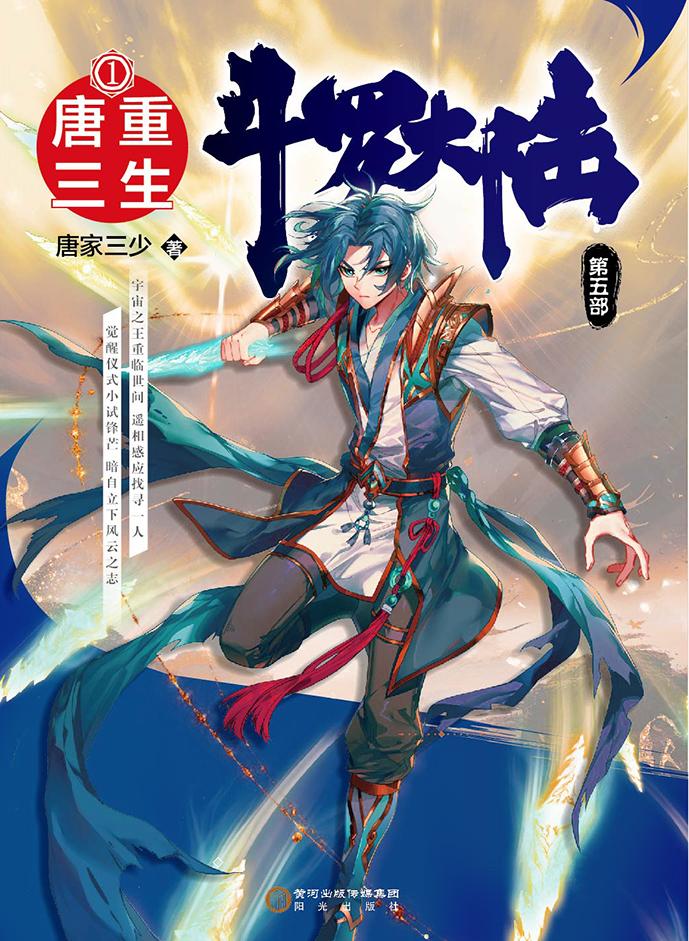奇书网>扫元txt在线阅读 > 第159章 史诗级任务(第2页)
第159章 史诗级任务(第2页)
周闻道见石山的面色突然沉凝下来,疑元帅不高兴,想起还有好消息没来得及汇报,忙道:
“元帅,属下此行虽然遭遇了一些波折,却也带回了数位人才。”
石山一听“人才”二字,果然精神一振,眼中精光乍现,急道:
“快说说,是何等人才?”
周闻道之前就为石山招募过匠人,深知元帅求才若渴,无论文武,凡有一技之长者皆在延揽之列,士农工商概莫能外,遂道:
“属下方才提到的船主杨破浪,此人熟悉前往大都、高丽、日本等地的航线,操舟之术远胜常人,更兼擅修船。经他牵线,咱们还招募到了两名造船匠人。”
“好!此事办得极好!”
石山击掌而赞,这简直是瞌睡碰上了枕头。
自己正筹办巢湖水军,周闻道就送来了造船匠人,巢湖短期内肯定是没条件造大舰的,这些匠人留在红旗营,暂时有些大材小用,但谁又会嫌手下的专精人才多呢?
“此外,指挥还在动乱中救下了一位世外高人。方国珍焚港之后,属下……”
周闻道将施耐庵当日的精彩论断复述了一遍,尤其推崇“驱使饥军”南下平乱的奇策。
石山听罢,顿时乐了。
施老爷子不愧是写小说的,脑洞就是大,竟然能想出这等看似能“中和”两难的平乱之策。
可惜,此策乍听奇崛无比,细究之下却满是疏漏。
所谓纸上谈兵,不过如此。
大军调动若真有如此容易,那原本历史轨迹中的大明,又何至于在流民与边患的反复折腾下轰然崩塌?
不过,此人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石山正有用得到他的地方。
“施夫子现在何处?”
周闻道不清楚石山的想法,见元帅追问,只道是被施耐庵的奇谋所吸引,想到又为元帅发掘一才,心中喜悦难抑,忙道:
“就在城中馆舍安顿。”
石山此刻正好得闲,既然决意用施耐庵,那就尽快找到其人来谈一谈。
“速请!”
元帅府自有亲兵、吏员负责奔走传唤,用不着周闻道自己去。
周闻道还有一件事没有回报,便不急着告退,道:
“元帅,属下归途中探得,元廷已经降旨查办了彻里不,命诸王秃坚领从官百人、骑兵一千,日夜兼程赶赴扬州。”
“嗯。”
石山点头,示意自己知晓了此事。
彻里不怯懦无能,未战先溃,白白葬送数千兵马,更让红旗营顺势攻取了滁州,致使扬州路形势大坏,如此泼天大过,元廷若还不惩处,岂不是寒了天下忠臣义士之心?
但元廷不顾途中道路不宁,强令秃坚快马赶赴扬州履任,为了保证其人能尽快掌握局势,还特许他领从官百人骑兵一千赴任,就已是大大悖离了“惯例”。
看来,滁州一战,已经让元廷真正看到了红旗营的锋芒,对扬州路失陷的恐惧,竟迫使其打破常规,特事特办了。
实际上,元廷不仅加强了扬州路的军力,更在彻里不兵败后,火速下诏置安丰分元帅府,构筑针对红旗营的外围封控圈的意图,不要太明显。
石山迅速消化了这则情报,目光再次欣慰地落在周闻道和云身上,暗道果然做大事能历练人。
“刘家港既毁,方国珍麾下海贼实力又进一步壮大,元廷短时间内怕是很难恢复海上漕运。接应我亲族之事,暂且搁置吧。你们各有重任,不能把时间一直浪费在这件事上。”
周闻道为此准备了很长时间,却不愿就此放弃,道:
“元帅,属下途中听施夫子无意间提及,他近年曾行走于淮东,似有门路能弄到出海的船只。属下恐泄露军机,途中未敢深问。元帅此番招他来,何不亲自问他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