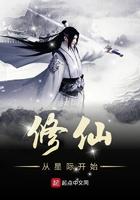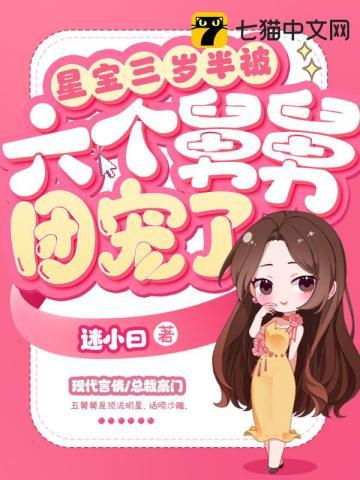奇书网>扫元江湖野人 > 第185章 昔日袍泽来相问(第4页)
第185章 昔日袍泽来相问(第4页)
“进城!救俺们的兄弟!”
白不信一行十一人,一人五马,昼夜不息,向南狂奔。沿途所见,皆是荒芜的田野,废弃的村落,偶尔遇到流民,也是面黄肌瘦、眼神麻木,看到他们这些带刀骑马的,远远便惊恐地躲开。
当他终于抵达濠州地界时,眼前的景象让他疲惫的精神为之一振。
虽仍是乱世,但气氛明显不同。官道上,有红旗营的巡逻小队警惕地巡视;田野间,农夫在有序地耕作,虽然衣衫依旧破旧,但眼神中少了麻木和绝望,多了几分对土地的专注和对未来的期盼。
沿途的村落,虽然也显破败,但能看到修补的痕迹,炊烟袅袅,透着一股顽强的生机。
这与他一路行来所见的死寂与凋敝,形成了鲜明对比,更坚定了白不信投奔石山的决心——或许只有石元帅这样的雄主,才能终结这乱世,才能给众多追随者大富贵。
待进入濠州城后,白不信又敏锐地感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繁忙。
街道上,车马辚辚,满载着箱笼行囊;许多挂着元帅府x司、x曹字样牌匾的官署门口,人来人往,搬运文书物品;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临行前的躁动与喧嚣。
白不信心中咯噔一下:难道来迟了?石元帅不在濠州?
果然,在濠州留守府外报上徐州李喜喜的名号求见后,他被引入了府中。
留守府内陈设简朴,却透着一股武人的干练。红旗营忠武卫都指挥使、濠州留守孙逊端坐主位,他约莫三十许年纪,面容刚毅,自有一股沉稳威严的气度。
听完白不信禀报的紧急军情,孙逊眉头微皱,徐州局势之糜烂,远超预期。他沉默片刻,抬眼看向眼前这个虽然疲惫不堪,眼神却依旧透着精悍与期盼的汉子,沉声道:
“白兄弟一路辛苦了。只是……”
他顿了顿,道:
“元帅已经移驾合肥。你等远道而来,不熟悉本地路径及我军哨卡规制,不可在红旗营境内纵马疾驰,以免引发误会。今日便先在馆舍安歇,不要乱跑。”
白不信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一路上的疲惫仿佛化作了冰冷的铅块压在胸口。见不到石元帅本人?那千户的重托,自己拼死奔波的辛苦,还有那五十余作为敲门砖的战马,岂不都要落空?
他强忍着内心的焦灼,抱拳,急声道:
“孙都指挥使!小人此来,除了刚才所说之事,还有一些,一些关于徐州红巾军内部,李千户的旧事隐情,需得当面向石元帅陈情,方能说得清楚明白!事关重大,恳请都指挥使务必行个方便!”
他的语气带着近乎恳求的急切,目光紧紧盯着孙逊。
石山非常重视防盗防谍,尽管红旗营治下,暂时还不具备重建乡村基层组织的条件,但对外来兵马的监控已经极严,不允许白不信等人随意深入境内,乃是制度要求。
孙逊作为留守大将,严格执行制度,不让白不信等人自行深入,是职责所在。
不过,他作为濠州留守,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责,就是甄别对待徐州红巾军溃散或主动投靠的势力,前几日才在合肥面见过元帅,得到过石山明确的指示。
眼前这个白不信眼神清正,言语间条理清晰,显然是李喜喜精心挑选的心腹。他带来的军情紧急,李喜喜的投效之意也相当明确,还奉上了颇有分量的信物和厚礼。
更重要的是,孙逊从白不信那极力压抑却依然流露出的热切眼神中,看到了一个底层军官渴望抓住机遇、改变命运的强烈意愿——这恰恰是红旗营能迅速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孙逊沉默片刻,笑道:
“白兄弟误会了。非本将有意阻拦。实是军规森严,不可轻废。”
旋即,他话锋一转,道:
“不过,你来得倒也巧。明日一早,拔山卫便要护送部分人员及物资前往合肥归建。你们可随胡将军同行。有我军大队兵马护送,行程安全无虞,也省得你们不识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