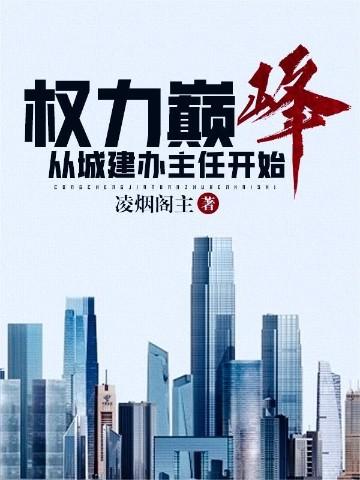奇书网>扫元在线阅读 > 第244章 钟山风雨起烽火(第2页)
第244章 钟山风雨起烽火(第2页)
徐继宗生性谨慎,虽然料定贼军上山的兵马少,警惕性差,却没有被可能到手的功劳冲昏头脑。
即便决定出击,依旧在寨堡中留下了两百士卒坚守,将其余近一千八百名官兵尽数带上。
他的目的并非与这五百红旗军硬碰硬——其他各寨堡依险而守,都挡不住红旗营,他徐继宗还没狂妄到以为凭千余人就能正面击溃对方。
而是想借助山林密布的复杂地形设伏,试探一下这支声名赫赫的军队的真正斤两,若侥幸成功,自是意外之喜;即便不成,也能凭借地利迅速撤回寨堡。
……
山间,淅淅沥沥的细雨已然停歇。被雨水洗涤过的空气格外清新,带着泥土和草木的芬芳。但行走在其间的将士们却无暇享受这份清新,他们的衣甲早已被雨水和汗水浸透。
钟山南坡山腰处,常遇春停下脚步,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抬头望向北坡上方隐约可见的元军箭楼轮廓,浓眉微蹙,语气中带着几分懊恼,道:
“大意了!俺原以为随便选个方向就能直插山顶,没想到这七拐八绕的山路这么难走!今日上山的时间太晚,看来是没法登顶了。走,到前面那个山头去看看,能瞅清城中大概动静,咱们就撤!”
护卫在他身边的营指挥使是赵伯仲,便是那位曾智取舒城立下功劳的舒城人。
赵伯仲闻言却没有立即应声,目光锐利地扫向前方常遇春所指的那片山林。那片林子异常茂密,在雨后的薄暮中显得有些阴森寂静,他凝视了片刻,谨慎地开口,道:
“都指挥,且慢。前方那片林子……似乎有些不对劲。”
“嗯?”
常遇春停下脚步,顺着赵伯仲的目光望去,却没发现什么异常,疑惑道:
“你看出什么名堂了?”
赵伯仲伸手指着那片山林的上方,低声道:
“都指挥请细看,那片林子上空,是否漂浮着一层极淡极薄的雾气?与其他地方似乎有所不同。”
常遇春眯起眼,凝神仔细观察。果然,那片茂林上空,确实萦绕着一层若有若无极其稀薄的雾气,若不集中注意力,极易被忽略过去。他有些不解,道:
“山林间有些许雾气乃是常事,雨后更是如此。你如何能断定那边不对劲?”
赵伯仲没有直接回答,他其实也不能肯定那边有埋伏,转身,看向常遇春身后的将士们,道:
“都指挥请看,弟兄们冒雨行军爬山到现在,里外衣袍早已湿透。此刻雨水虽然停了,但兄弟们体内阳气升腾,正在不断蒸烘衣袍,便会散发出水汽。
人数一多,聚集在一起,自然就会形成这样一片淡淡的雾气。”
常遇春回过头,果然看见身后的将士们个个额冒热汗,头顶热气氤氲,整个队伍上空的确凝结着一片类似的薄雾。他恍然大悟,蒲扇般的大手一拍赵伯仲的肩膀,发出赞许的大笑:
“嘿嘿!赵大郎,可以啊!眼毒,心细!难怪元帅时常夸你好读书,肯动脑筋,将来必有大出息!今日一见,果然不错!”
笑声未落,常遇春却没有下令队伍戒备或绕行,反而迈开大步,竟是要朝着那片可疑的山林继续前进,显然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赵伯仲顿时急了,连忙抢上前一步阻拦,道:
“都指挥!既知可能有埋伏,为何还要去探?”
常遇春却是豪气干云,浑不在意地笑道:
“俺们今日上山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勘察这钟山的地形地势,窥探江宁城防虚实吗?不登上前面那个山头,如何能看清城中全貌?
区区几个藏头露尾的毛贼,岂能吓得住俺?正好活动活动筋骨!”
赵伯仲深知这位上官的脾性,勇猛无畏,最是喜欢身先士卒。为此没少挨元帅的骂,他知道硬劝不住,只得退而求其次,恳切道:
“既然如此,可否让末将带领一队弟兄在前为都指挥开路?”
“胡闹!”
常遇春想起石山多次叮嘱他身为主将不可过于涉险,学着石元帅的语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