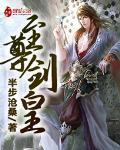奇书网>扫元在线阅读 > 第222章 人心向背脚投票(第2页)
第222章 人心向背脚投票(第2页)
李保儿重重地点头。战乱和灾荒最能磨炼人(扛不住的已经被自然“筛选”掉了),年仅十三岁的少年,眼神里却已有了远超这个年龄的成熟和对生存的极度渴望。
他之所以看到西进的船队后,就急着跑来告诉李贞这个消息,内心深处其实就是想劝父亲尽快离开盱眙这块绝望之地,去西边寻找一线生机。
接连不断的灾荒加上战乱,使得江北大地民不聊生,饿殍遍野。
若说这周边方圆数百里还有一块能让人喘口气,看到一点活路的地方,那恐怕就只有传说中的红旗营治下了。那里的传言很多,最诱人的便是“人人有饭吃”。
传言或许有夸大之处,就如同官军的战报经常胡编乱造,但战线不会说谎。
红旗营的地盘在不断扩张,官军节节败退,甚至一些被赎回的战俘带回来的消息,也或多或少证实了那些传言——至少在红旗营那里俘虏都能有口吃的,那普通百姓的日子,总不会比这边更差吧?
至于能不能吃饱?
这年头,能不饿死就已经是老天爷开恩了!
就连官军营中的军爷们,没仗打的时候,不也常常饿肚子吗?
李贞最终并没有进城,因为就在城外,他便从人们压低声音,却又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交谈中,听到了一件事:
官军和红旗营正式停战了,城中有不少商号掌柜急不可耐押上自己的货物,前往五河发财。
三三两两面黄肌瘦的百姓聚在背风的土墙根下,交头接耳地讨论着,要不要也趁着这个机会,冒险往西边跑,去五河那边讨条活路。
李贞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他比这些家里或许还有点存粮,尚能再咬牙熬一熬的乡人们不同。
他是家无余粮,地无根苗,是真的一天也熬不下去了!
李贞当即返回自家那间四面透风的破败茅屋,拉起儿子,将仅有的两床破烂不堪的被卷起来,又带上那口烧得发黑的铁锅和几个豁口的瓦碗,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父子俩没有多做犹豫,趁着天色尚未完全黑透,便踏着冰冷的土路,连夜离开了这片给予他们无数痛苦记忆的土地。
李贞原本以为自己行动已经足够果决,应该能赶到众人的前面。
没想到,出了盱眙地界,走上通往西面的荒僻小道时,竟还能遇到三三两两同样拖家带口,背着简单行李往西去的流民。
大家都是同样的面黄肌瘦,同样的惶恐眼神,却又带着一丝奔赴新生活的希冀。
战乱之中,人退兽进,荒野中潜藏着无数的危险,寒冷和沼泽很容易吞噬不熟悉地形的陌生人,饿狼、野狗等野兽,也可能要了二人的小命。
但李贞父子却不敢离这些陌生的流民太近,只是远远地跟着——因为他们深知,有时候饿极了的人比野兽更加可怕。
而且,官军虽然面对红旗营节节败退,但在五河方向却是以攻代守,沿途修建了不少寨堡和烽燧,李贞不确定这些地方的官军老爷们,会不会眼睁睁看着治下的“丁口”逃往敌境而不管不问。
果然,途经刘台堡时,汇聚起来的流民已经达到了近百人,动静终于引起了堡中官军的注意。
一队穿着破旧军袍的官兵骂骂咧咧地冲出来驱赶,呵斥众人返回原籍。这些可怜的流民早已一无所有,好不容易看到了生的希望,哪里肯轻易回头?
有人情绪激动,忍不住出声争辩了几句,立刻遭到了官兵的残酷镇压。
棍棒刀枪毫不留情地落下,冲突中,当场就有近二十个流民被打死打伤,鲜血染红了枯黄的草地。剩余的流民吓得魂飞魄散,哭喊着四散奔逃,如同受惊的鸟兽。
李贞和李保儿早早地就躲进了远处一片茂密的枯草丛中,大气也不敢出,眼睁睁看着这血腥的一幕,久久无语,只有心在剧烈地跳动,充满了恐惧和后怕。
好在过了刘台堡这道关卡,越是靠近红旗营的实际控制区,官军反而变得越发“克制”起来。
沿途哨卡和寨堡里的官兵,即便看到有成群结队的流民从他们的防区外经过,也大多只是冷漠地看上一眼,很少再出来强行阻拦或打杀。
或许他们自己也清楚,这片糜烂的土地强留不住人心,也或许是他们得到了某种不成文的命令。
如此,提心吊胆连续跋涉了六日,李贞父子跟着一股新的流民队伍,终于踉踉跄跄地踏入了五河县的地界。
在这里,他们看到了更多汇聚而来的流民。很多人为了避开官军的重点封锁区域,先绕道无人控制的虹县,再艰难南下,途中经历的凶险和艰辛,自不必说。
但至少这条路线里,他们不用再时刻担心被官军如同猪狗般随意打杀。
五河县的红旗营军民,显然对于接收和安置流民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在进入辖区的要道口,设立了临时的流民接收点,支起了几口冒着腾腾热气的大锅,锅里熬着虽然粗糙却香气扑鼻的杂粮粥。
所有流民都必须先排好队,完成简单的登记造册,然后才能分到一碗浓稠滚烫的救命粥。
现场有手持兵刃的红旗营将士维持秩序,眼神锐利,纪律严明。
若有不开眼的流民仗着身强力壮或者人多势众,不想排队,甚至试图抢夺他人那份来之不易的食物,这些将士会毫不犹豫地出手,用刀枪和拳头教他们遵守这里的规矩。
惨叫声和呵斥声偶尔响起,迅速地将骚动镇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