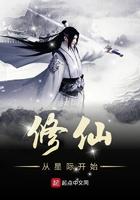奇书网>扫元在线阅读 > 第180章 兵临合肥守军惧(第3页)
第180章 兵临合肥守军惧(第3页)
“对!狗都不回去!”
“石二哥说得对!俺们有钱了!”
“离了那鬼地方,俺们自己过活!”
其他亲友也纷纷应和,绝望和恐惧渐渐被一种新生的希望和决绝所取代。
石二河看着大家重新振作起来的精神,心中稍安,朝李初八用力点了点头,正准备再说些什么,目光不经意间扫过波光荡漾的弥河河面。
就在这时,下游的芦苇荡里,一叶轻舟如同游鱼般悄然滑出。船头,一人长身而立,青衫在河风中微微拂动,不是那“周掌柜”又是谁?
石二河的眼睛猛地瞪圆了,激动得浑身颤抖,指着那越来越近的小船,声音因为极度的兴奋而变得嘶哑高亢:
“哎!快看,那不是周掌柜?哈哈哈!俺就知道,俺就知道三郎是真出息了,真出息了!”
当周闻道接上石二河等人时,在数千里之外的庐州路,石二河日夜牵挂的三弟石山,也刚刚结束了对六安城的整治。
桀骜难驯的豪强朱亮祖,最终还是认罪伏法了。
促使他低头的,并非酷刑或威吓,而是为了给其年仅四岁的次子朱昱留条生路。
至于朱亮祖的长子朱暹,已经死在了朱亮祖前面,死因是劫狱。
朱暹确实有乃父朱亮祖的几分血性和勇悍,年仅十三岁的少年,带着几个心腹家奴悍然劫狱,居然真的被他冲到了关押朱亮祖的班房门前,但最终还是倒在了距离父亲咫尺之遥的地方。
朱亮祖透过牢门栅栏,亲眼目睹长子咽下最后一口气,终于意识到一夫之勇,在庞大的组织力量面前是多么渺小。
他选择认罪,用自己残余的尊严和生命,换取幼子朱昱活下去的机会。
石山本就不是嗜杀之人,从徐州一路拼杀至此,惩戒过不少为非作歹的大户豪强,也不是所有人都斩尽杀绝。
更何况,朱昱年仅四岁,懵懂无知,对他也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
但他也没有将朱昱交给朱氏宗族,出卖朱亮祖最起劲的人中,就有不少朱氏族人。朱亮祖的发妻已于去年病亡,朱昱可以算作孤儿了。
石山将朱昱安置到了羽林营,与其他孤儿们一视同仁抚养,并亲自教导,还向朱亮祖做出承诺,此子将来若有出息,单开家庙,许其祭祀包含朱亮祖在内的先人。
当朱亮祖得知这些安排后,低头沉默良久,再抬起头,眼中已经没有了怨恨,只剩下一片死水般的平静,以及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最终只化为一句话“谢元帅给朱家留了一炷香。”
行刑之日,朱亮祖神色坦然,走得异常平静。
围观的人群中,有恨其往日跋扈者拍手称快,亦有唏嘘世事无常者摇头叹息。
若干年后,朱昱凭借自身努力高中进士,官至一省巡抚。朱氏父子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往事,被施耐庵的门生收录入《乱世英豪传·续》中,在坊间广为传颂,成为一段令人感慨的乱世奇谈。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石山之所以在朱亮祖父子身上费如此多的心思,自然不是因为对朱亮祖有什么成见——事实上,两人之前并无交集。
惩治朱亮祖,纯粹是就事论事,是对“朱亮祖”这个现象的处理。
元末乱世,像朱亮祖这样拥有一定能力,又野心勃勃的士绅豪强多如牛毛,即便红旗营最终打下了江山,这类人也不可能消失。
只要滋生士绅豪强的土壤依然存在,杀了一个朱亮祖,还会有张亮祖、王亮祖等等,不断冒出来。
石山深知,乱世之“乱”,不仅体现在经济崩溃、军事割据等乱象上,更深层的原因是“人心之乱”。
元廷对地方豪强长期采取一种近乎放纵的策略,在原历史轨迹中埋下了难以根除的隐患。其中最大的恶果之一,便是让这些士绅豪强的“心”彻底“野”了,再难约束。
就像现在,元廷为了拉拢他们,可以开出各种优厚条件,而这些条件,是石山永远都给不了的。
治乱世,单靠杀人是不够的,更需要“诛心”。
对朱亮祖的处置,尤其是对朱昱的安排,便是石山“诛心”之策的一部分。
处理完六安诸事,石山便率军拔营东进。大军旌旗招展,兵甲铿锵,沿着官道浩荡前行,很快就引发了合肥守军的极度恐慌。
此次南征,石山亲自统领西路军,攻取庐江、舒城、六安三城。
而东路方向,则任命邵荣为行军总管,统率合肥军(左君弼部)、含山军以及缺了冯国胜第二营的骁骑卫,进攻和州、乌江两城。
原本预计东路军的进展会更快,但元廷为防红旗营渡江与徐宋大军合流,向和州紧急增派了援军,导致邵荣部在乌江、和州一线陷入苦战,至今才艰难攻下乌江,和州仍在元军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