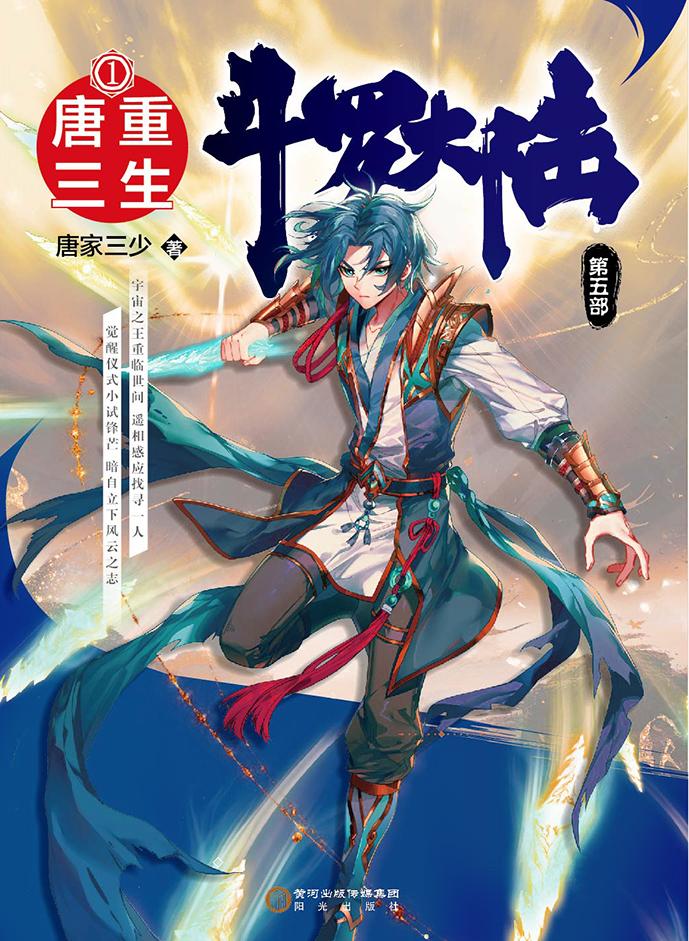奇书网>扫元在线阅读 > 第175章 战六安常冯联手(第3页)
第175章 战六安常冯联手(第3页)
陈通统率的庐江军虽然打退了“彭祖家”两次进攻,却是胜在地利人和,实际战力其实并不强。其部本就整训不足,又首次远离本土攻城,士气不高,遭敌军突击,伤亡较大很正常。
而后续战斗结果,则证明了六安守军阵战能力并不强,其部开始能够击穿陈通、费聚两部,主要原因还是其主将勇悍,又出其不意。
常遇春受挫后没有因怒兴兵,强攻泄愤,而是选择收拢部队,救治伤员,重整旗鼓,这份冷静,已让他立于不败之地。破六安,只是时间问题。
石山的目光重新落回眼前这位口齿清晰、观察入微的信使身上。此人汇报条理分明,对战场细节把握精准,还能分析出不同部队的伤亡原因和敌我战力特点,在什长一级的军官中,实属难得。
“听口音,吴什长是钟离人?可曾读过书?何时投军?”
扩营建卫后,石山下放的一些权力,比如什长由各卫自行选拔培训,只有队率及以上军官才需石山亲自把关,并须经过捧月卫军官轮训营。
吴国兴只是个什长,之前没能进入元帅法眼,今日卖力表现,就是为了引起石山关注。此刻,元帅相询,吴国兴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忙挺直腰板,恭敬回答:
“回元帅!末将正是钟离岗圩人,家中薄有田产,曾随乡塾先生开蒙数年,略识文字,粗通文墨。末将于今年三月初九,方投效义军,补充兵训练结束后,就在常都指挥使麾下效力。”
红旗营占据濠州后虽然一直征兵,但考虑到钱粮压力和实际需求,最初征兵规模并不大,直到吴六斤率队攻取怀远后,需要多线作战,石山才扩充了战训营,加大征募训练补充兵的力度。
吴国兴身材魁梧,举止沉稳透着练家子的底子,还“略通文墨”,显然是地方上的豪强或殷实之家子弟。这与当初徐达的境遇何其相似?都是初期观望,舍不得家业,不敢贸然押注红旗营。
直到三月份,石山击溃元将彻里不,完成八卫扩编,展现出割据一方的雄厚实力后,吴国兴才下定决心投军,错过了最初那波“从龙”扩编的升官潮,再想从普通士卒中崭露头角,难度陡增。
但此人能被常遇春派做信使,便是对其能力和见识的认同,石山自然也能看出吴国兴有潜力。
军队是大丈夫乱世立身之基,对有潜力的军官苗子,石山都不吝拉拢和培养,早已如吃饭喝水般成了本能,他见吴国兴一路疾驰而来,嘴唇干裂,浑身都是汗泥,形象颇为狼狈,扬声唤道:
“华云龙!”
“末将在!”一名与吴国兴体形相仿的年轻军官应声出列,目光炯炯有神。
“由你安排吴什长食宿,再将你的换洗衣服送一套于他。回头,我再给你置办一套。”
华云龙是定远人,今年刚好二十岁,鲁钱河之战后就被整编入邵荣所部,此后积功升至队率,接受军官轮训期间被石山看中,留其在捧月卫任职。
这种交流乃是红旗营成立之初就形成的惯例,也是石山压制麾下各山头的手段之一,不能积极适应这一套的营指挥使永远都别想再进一步。
而在这种轮训、交流中,大量真正有能力的后起之秀,却因为进入元帅视野,而能得到更多的培养锻炼机会,获得比常人更快的进步。
华云龙便是这一制度的受益者,留在元帅身边后,每日都充满干劲。
今日也是如此,一套换洗衣服,很不起眼的小事,却让吴国兴和华云龙都感受到了元帅对自己的重视,二人心潮澎湃,几乎同时单膝跪地,谢道:
“谢元帅厚恩(赏赐)!”
待华云龙领着难掩激动的吴国兴退下后,石山便命亲卫起驾返回城中,并命冯国胜在行辕等候。
石山虽然坚信常遇春必定能够攻克六安,但时局不等人。
安庆路“彭祖家”与元军激战正酣,江南徐宋政权已与元军和地主武装拉锯相持,徐州芝麻李仍被元军压着打,淮南行省兵马近期也出现在滁州、五河等地,红旗营的外部环境并不好。
更重要的是,大军西进,连接濠州老巢的咽喉要地——合肥,尚左君弼这个“杂牌”手中,还未纳入红旗营直接统治,主力顿兵六安城下的时间越久,风险就会越大。
回到行辕,冯国胜已经候着了。
“元帅!”
“国胜,”
石山言简意赅地告知了六安之战情况,又布置作战任务。
“伯仁小挫,左肩受创,但无碍指挥。六安军整体战力不强,唯朱亮祖此人狡悍,此战不宜迁延太久。你部今晚就做好准备,明日一早开拔。抵达后六安后,听从伯仁调遣!”
冯国胜闻战则喜,得知六安居然还有能击伤常遇春的悍将,眼中更是燃起熊熊战意。
“末将领命!定与常都指挥使同心协力,踏平六安,生擒朱亮祖,献于元帅帐下!”
……
注:三国时,庐江郡包含今安徽六安、舒城、霍山、庐江等市县及寿县部分地区,远非元末的庐江县可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