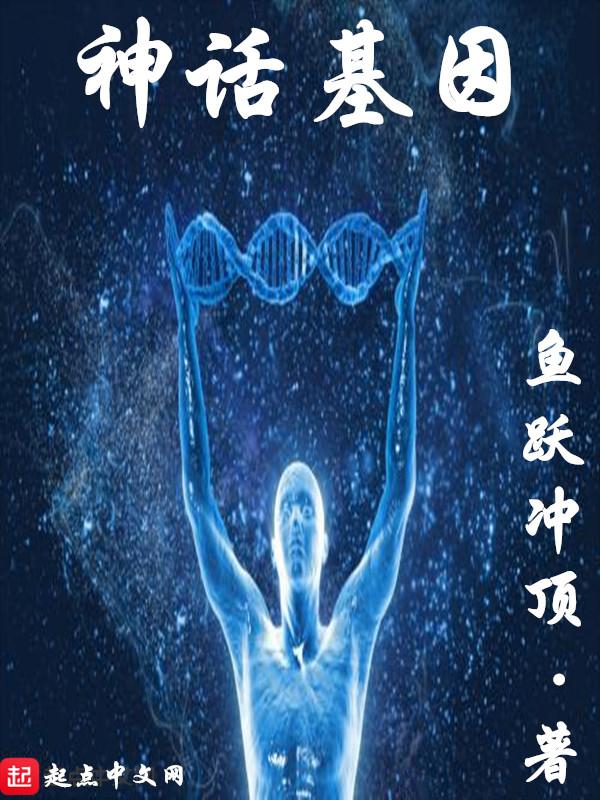奇书网>重生后成了帝卿白月光女尊作者雪岛23 > 100110(第13页)
100110(第13页)
袁缚雪又另起话头,“近日我在园中遇见太常院几名官员,皆是我汝南袁氏族人,由我母亲引荐。她们似在商议北秦之事。”
北秦,正是鲜卑所建政权。
当啷一声,姬怜手中茶盖跌入盏中。他紧盯袁缚雪,声线微颤:“她们商议什么?”
“与我大周相关。”
袁缚雪缓缓而道,“北秦如今有了位新可汗。她已向其神明腾格里请示,称未来王夫出自大周。特遣使团前来求亲,数月前已出发,如今恐将至建康。”
一股寒意直冲姬怜天灵,冻得他指尖发抖,连胸中气息都凝滞。
“此事早就递交到陛下手中,只不过陛下对此置之不理,一直未做决断。也许……”
袁缚雪以指蘸水,在石案写下人选二字,“是在斟酌究竟从世家择郎,还是自皇室挑选。”
此话一出,他转眸看向姬怜,却怔住了。
他从未见过姬怜有如此失态的时候。
姬怜眼眶蓄泪,唇色惨白,眼中恨惧交织如浓雾翻涌。他狠狠地咬着下唇,“为何我至今未闻风声?”
“此事目下仅太常院几位高官知晓。”袁缚雪轻拍他脊背安抚,“不必过忧,未必会选中你。况且陛下正为凤阁所提土断之策烦心,暂且无暇他顾。”
恐惧就如同蚂蚁上身一般,密密麻麻地爬满姬怜的全身,梦境里如同狗一样在地上爬的屈辱画面再度席卷而来。
姬怜倏然起身,唇齿微颤,“我要去找……”
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个人选便是谢廷玉。可是即使谢廷玉知晓此事,要如何帮他?更何况现在人选都未敲定,他怎么能拿这种还未确定的事去烦她。
话音戛然止于喉间,化作无声哽咽。
袁缚雪也随之一同起身,蹙眉道:“你要找谁?是陛下?”
“我……我不知。”
姬怜手指紧紧地扣着石案的一角,指节泛白,“我、我先告辞了。”
他对身后袁缚雪的呼唤充耳不闻,如游魂般蹒跚于宫道。抬眼望见前方一座高阁,便恍惚拾级而上。
待至顶层凭栏远眺,忽见一人正自宫道尽头缓步而来。沿途宫侍皆笑靥盈盈,齐声唤道:“谢大人日安。”
谢廷玉是被姬昭下急诏唤到皇宫里的。
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姬昭派下去的人根本无法推进由凤阁统一议定的土断之策,甚至连世家的门槛都踏不进去,偶尔得以进入,也往往被推诿搪塞,三言两语便被绕得晕头转向,再多问几句,便觉有脑袋和身体分家之虞。
姬昭气得直将案上的奏章掀翻,踩在脚下,声如霹雳:“这些世家当初不是在凤阁里说得好好的?怎么到真要推行时,却又百般掣肘!”
她猛地一指殿外,厉声怒喝:“是不是这件事没有谢氏,就无人能成?!朕就想问问!”
殿中怒火翻腾,热浪扑面,伺立左右的秉笔使,宫侍等人尽数匍匐在地,背脊冷汗涔涔,谁也不敢多言半句。
良久,姬昭强压怒意,命人急召谢廷玉入宫。
谢廷玉一路行至华盖殿,甫入殿门,宫侍已忙不迭跪下替她解去靴履。她只着一双素白袜履入内,举止沉稳,拱手行礼:“臣见过陛下。不知陛下急召,所为何事?”
姬昭见谢廷玉双手恭垂身侧,神色沉静,心中怒火因这位功勋卓著、深得民心的重臣依旧持重如常,竟消散大半。她缓了神色,一指流苏坐垫:“谢卿请坐。”
谢廷玉未动,再拱手道:“臣惶恐。还请陛下明示。”
姬昭更加满意了。
“朕近日推行的土断之策屡屡受阻。谢卿作为此策首倡者,有何见解?”
“陛下,此事是否能成,只在于陛下。”
“谢卿细说。”
“陛下仁厚宽宥,近侍皆耳濡目染,纵有特权亦行事温和。”
姬昭目光微动,被这句话哄得怒意又减三分。
“臣愿为陛下分忧,以雷霆之势迫士族就范。若有抗命者,必以武力慑服。”
姬昭闻武力二字略显迟疑:“然金吾卫等禁军需护卫皇城,不宜介入地方事务。”
“陛下无需动用禁军。”
谢廷玉从容应道,“只需赐臣特许令,建康内外诸郡县,臣皆可为陛下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