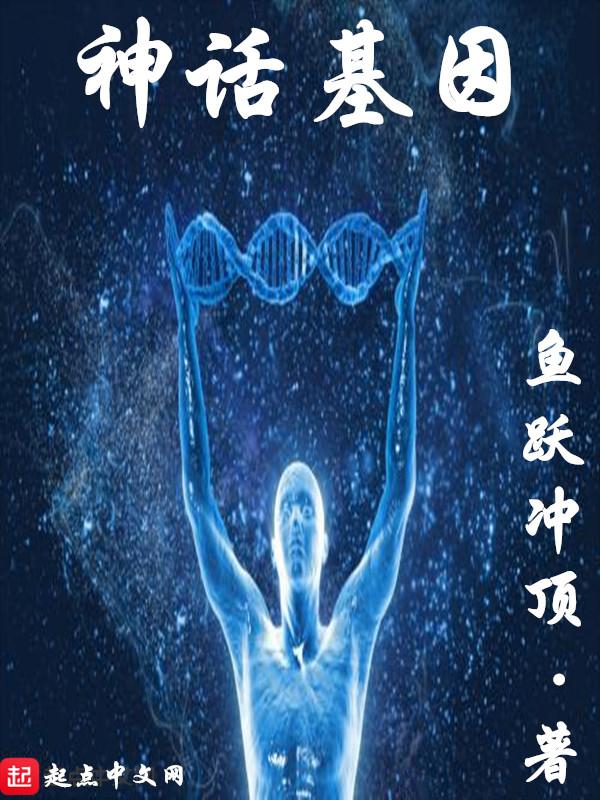奇书网>寐前欢by罗敷媚歌 > 90100(第12页)
90100(第12页)
夜深了,狭小的营帐中点着烛,烛火颤颤,暖意游曳在寒夜里,云央小心翼翼地给熟睡的姐姐掖了掖被角,指尖不小心触及姐姐嶙峋的锁骨,那雪白的皮肉只覆在上面薄薄的一层,云央的心霎时揪紧了,胸臆中涩塞难言。
姐姐怎么被磋磨成这个样子【踏雪独家】了……
当时在那高塔,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面前瘦骨嶙峋被包裹在繁复神袍里的人竟然是自己苦苦寻觅的姐姐,刚要靠近,就被那高大的男人一掌打了回来。
她都没看清对方是怎么出手的,也没有看到对方有什么兵器,就重重跌在了地上。
后来,她竭尽毕生之所学,一招一式也总被对方轻易拆解,云央心里知道,若不是那个神族祭司点头,她根本带不走姐姐云嘉。
力量如此悬殊,她若想为姐姐报仇,那便是天方夜谭了。而薛钰此行南诏是为了搬救兵,即便她想狐假虎威,也不是时候,只得灰溜溜的就这么走了。
可是如今看着姐姐苍白的脸,云央又气又无奈,第一次对力量、权势生出了渴望来。
真想灭了南诏,杀了那劳什子祭司,方能解心头之恨!
喝了安神汤,云嘉睡的尤为踏实,紧蹙的眉头松开了。
小泥炉烧的正旺,一方营帐内有种昏昏然的温暖,云央捂住因心疼姐姐而钝痛的心口,像只小兽,极其依赖地趴在了姐姐身上。
还好,她找到了姐姐,待这边事了,路都通了,就带着姐姐回去享福。
忽然一阵巨响,云央慌忙捂住了姐姐的耳朵,好在云嘉仅是蹙了蹙眉头,便又沉沉睡去。
云央悄声起来,蹑手蹑脚地跑出去,只见她们的营帐不远处聚集了好些人,都垫着脚或踩着石头看向火光冲天的蜀州城。
“这是在火攻吧?马上就要突破了,惠王殿下横扫逆臣叛军,真是应运而生救我们于水火啊……”
“我听说今夜若是攻破了那些逆党最后的防守,就是赢了。火攻这法子好像是惠王殿下身边那个谋士想出的法子。”
“什么谋士,人家本来就是皇帝派来的大官,说是什么世家子。”
“世家?跟咱们城里那个张家一样,这能想出什么好法子?”
“此世家非彼世家,薛家可是经历了数代沉淀下来的书香门第,每一代都是实实在在历经科举选出来的,可不是门阀或者地方豪强,真正的文人精华之所在。”一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解释道,“薛大人虽是个文人,却不是你们想的那种书呆子,此时就在城中坐镇,此仗定能赢的。”
“还有好些人没出来呢,这火攻了之后咋整啊……”又有人担忧道。
云央安顿好姐姐,找白日里的大娘帮她看着点,便拿起长枪往蜀州城去了。
来蜀地两三日了,她都没想着进城去找薛钰,便是不想耽误他的正事,而且此时正是战事胶着的时候,他也顾不上她呀,她又不是什么需要人照顾的幼童,便自己带着姐姐在营地住了下来。
说不担忧,是假的,这几日从流民的只言片语中,她隐隐窥见了城内的战况的凶险。
既然这是最后一仗,她要去看看,就看一眼也好,不能让他出任何岔子。
第96章“不做”
硝烟弥漫,蜀州城内火光冲天,远远望去,那一片的夜空都发亮。
“薛大人,找到您夫人了,就在半坡大营里,我们过去领人,夫人不见了,只有夫人的姐姐在。”侍从低声道。
一向清冷淡漠的文人面色微变。
在这等战乱时侯,他若想在流民中找一个人太难。但云央若想找他,并不难。
可她没有找他。
薛钰在桌案上摊开舆图,耐着性子指挥下属接下来的布防。
这场战乱已到了尾声,还有许多事需要善后。比如大皇子押解归京后该如何处置,比如在这场叛变中,那些死去的官员家人按忠臣之后还是逆党处置,比如蜀地的战后重建……
还有那万俟神族大祭司望舒,罪不可恕!
刺史府紧闭的大门汩汩溢出鲜血来,混着雨水泥泞,蜿蜒到地面上,连石阶被染得血红。
“禀告薛大人,前门后门皆已堵死,里面的叛臣逆党插翅难逃!”
惠王的南境军如雷霆破竹般瓦解了大皇子李泓与前朝余孽的乌合之众,只剩数百余叛臣和匪首藏匿于这刺史府内。
“只是里面、里面还有蜀州通判李大人的妻女,李大人和他四个儿子在昨天全都战死了……”
惠王约莫四十左右,身形挺拔彪悍,浑身散发着一种令人胆寒的气息,那小声求情的士兵声音渐次低了下去,连一旁交头接耳的议论声都归寂于无。
惠王久经沙场,身上已有了杀气,连他身侧的马都不安地喷着鼻息。
一双修长的手按住马颈,只见那清隽的文人神色平静道:“按原计划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