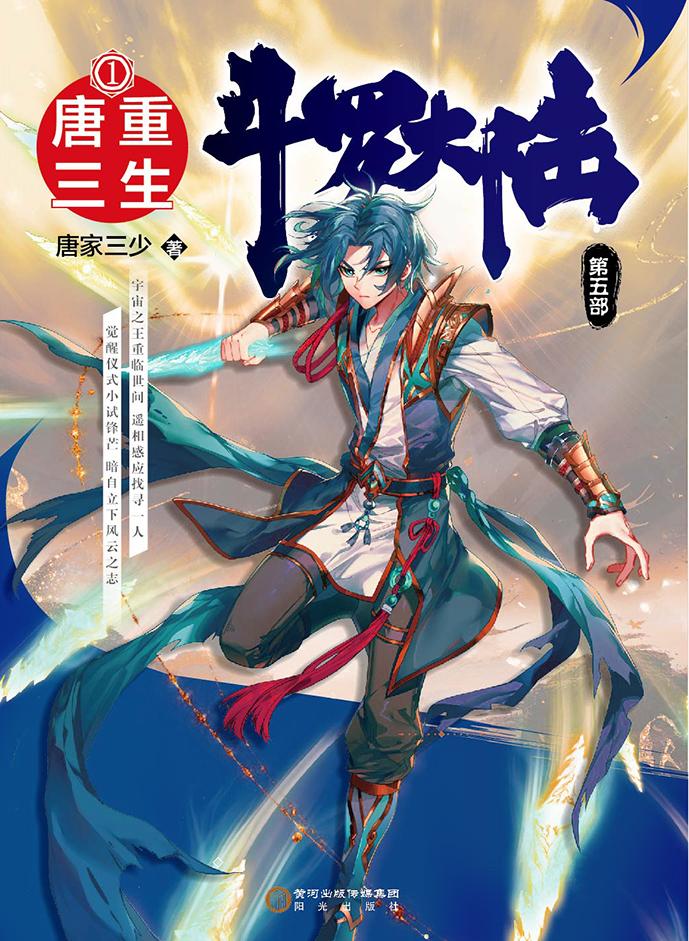奇书网>我在夺嫡文里开养猪场免费阅读 > 100110(第30页)
100110(第30页)
“隐王妃?本宫知道你,卫国公唯一的外孙,听说你和七皇子成婚后,也是恩爱夫妻。”
谈轻嗅觉敏锐,不大喜欢这佛堂里浓郁的檀香气味,闻言眉心一紧,“你知道裴折玉要干什么?裴折玉今日出行宫,也与你有关。”
他陈述的语气俨然已经确定此事与祥妃有关,如果不是这样,祥妃不会一见到他就问裴折玉有没有动手,既然如此,他也没必要再保持那所谓的礼仪了,谈轻定定看着祥妃,“祥妃,你们到底是要干什么?”
要是祥妃不愿意回答,谈轻悄然捏紧五指,他不介意话一点精神控制,得到想要的答案。
祥妃却没有看他,而是一脸虔诚地双手合十,朝着观音拜下,唇边还挂着怪异的笑意,口中喃喃:“愿七皇子得手,让我儿归来。”
谈轻挑起眉梢,祥妃只有一个亲生的女儿,那就是宁安公主,可是宁安公主早已经去漠北和亲,如今也十多年了,怎么可能回来?
那么裴折玉一定是在做很危险的事情,难不成……
谈轻睁大双眼,惊愕而又不可思议地看着祥妃,“宁安公主是漠北王后,寻常事回不来。”
祥妃像是听到什么笑话,忽然轻声笑起来,泛着血丝有些浑浊的眼睛却透露出几分恨意。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但若是国丧,她会回来的。”
还真让谈轻猜中了,他心下震撼,“你们想要杀皇帝?你们疯了?裴折玉现在在哪里?”
和亲公主嫁到漠北,成了漠北王后,理应是一辈子都不会回来了,但若是国丧,皇帝死了,宁安公主没准真的能回来,她可以用回来见父皇最后一面的借口,而漠北也可以借送她回来打探朝中局势……
可谈轻想不明白,祥妃这么疯是为了见女儿,那裴折玉呢?裴折玉为什么要跟她们胡来?
谈轻道:“你们这是弑君!”
“弑君?哈哈哈……”
祥妃反而笑得越发开心,笑着笑着,她脸上露出一抹狠色,“若不是他,宁安也不会小小年纪就被送去漠北,他拿我唯一的女儿顶替他最宝贵的大公主,我的女儿又该怎么办?”她回头看向谈轻,质问道:“我不该恨他吗?我不该怨他吗?我的宁安,也是他的女儿啊,他对大公主那样宝贝,为何就不能也怜惜一下我的宁安?”
“十几年了,我的宁安自从去了漠北,十几年来音信全无……”祥妃眼眶泛红,含恨的语调带上几分哽咽,“她走的时候还那么小,她说过她不想去和亲,可是没有在意她,没有人在意我们母女分离有多痛!”
她扶着胸口的手因为激动开始颤抖,“若没有意外,这辈子她都不会回来了,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女儿了,我甚至不能说出他们拿我的宁安替换大公主的真相,我被软禁在钟粹宫中,在他们口中得了癔症……”
祥妃笑起来,笑容讽刺而又幽怨,“他们这样对待我和宁安,我便是弑君,那又如何?”
谈轻知道她恨皇帝和大公主,对她弑君只是有点惊讶,但也能理解,可他还是想不通。
“那裴折玉呢?”他追问道:“他现在又在哪里?”
祥妃轻呵一笑,脸上讥讽更甚,似乎早已料到果然不会有人在意她这渺小的恨意,她扶着香案一角,消瘦单薄的身体靠在上面,神情变得冷漠,“七皇子吗,他可是要比我更恨裴璋,更想亲手杀了裴璋。”
裴璋,是皇帝的名讳。
谈轻问:“为什么?”
祥妃讥笑道:“你是七皇子的枕边人,他都没有跟你说过吗?也罢,这是时辰他们应当都已经离开了,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
谈轻皱眉,“他们?他们在哪儿”
且不管他们都是谁,谈轻只想知道裴折玉在哪里。
祥妃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轻舒一口气,回头看向谈轻,方才的失态变作冷漠,“看来你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那你也拦不住七皇子,他要杀裴璋,是为了替他生母报仇。”
谈轻顿了下,“生母?”
他福至心灵,想起祥妃上回碰见裴折玉时说的话,再想到那副画像,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宁贵人?”
“隐王妃果然聪明。”
祥妃话中夸赞着谈轻,笑容很是嘲讽,“宁贵人?不,她不是宁贵人,她是宁氏,是御史唐锦林的小儿媳妇。我还记得,裴璋刚登基没多久,有回出宫解闷,碰见了唐御史府中新过门的儿媳妇,便看上了人家,让太后派人将宁氏请到宫宴上……”
她嗤笑一声,摇头道:“入了后宫,宁氏还不是任他鱼肉?本来好好的御史家少夫人,被按上我钟粹宫宫女的身份,成为裴璋的宁贵人,君夺臣妻,多荒唐啊,可他是皇帝,天下没有人敢说他的不是。”
谈轻知道当务之急是先找到裴折玉,可在此时此刻,也不着痕迹皱紧眉头,“然后呢?”
“然后……”祥妃微眯起眼,回忆道:“然后啊……听闻宁氏与夫君是青梅竹马的少年夫妻,十分恩爱,被裴璋强夺入宫,自是不愿,她到钟粹宫第一天便撞柱自杀,裴璋便拿她的夫家要挟,她才乖顺了些。”
那时祥妃还是祥嫔。
她还记得,她听皇帝的吩咐去劝过宁氏的,当她走进关着宁氏的房间时,她见到年轻的宁氏被五花大绑捆在床上,双眼含着泪哀求她帮帮自己时,祥妃是这么说的——
这天下都是皇上的,他想要你,谁又能阻止?
然后皇帝拿宁氏的夫家一家十几口威胁宁氏,她作为钟粹宫主位,看着皇帝平日悄悄来宠幸宁氏,却不敢出声,只拉着宁安公主躲在自己的寝殿中,也不敢再看宁氏那双逐渐没了光,只剩死寂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