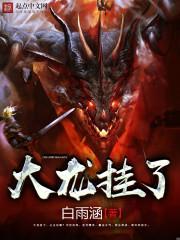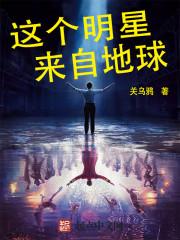奇书网>大哥这狗认为在训你啊笔趣 > 第403章 再暗示就真社死了(第2页)
第403章 再暗示就真社死了(第2页)
而在广州,那位自闭症女孩猛地站起身,走到镜子前,看着自己颤抖的嘴唇,第一次清晰地说出了三个字:“我……爱……你。”
与此同时,贵阳总部地下三层,伦理委员会紧急会议室的大门缓缓开启。一群西装革履的专家鱼贯而出,脸色各异。其中一人手中捏着刚打印出的报告,标题赫然是《关于Ω链社会效应再评估:从“风险失控”到“集体疗愈”的范式转移》。
走廊尽头,一名年轻女研究员拦住他们,声音坚定:“各位,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如果技术的目的不是控制,而是让人重新学会倾听彼此,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阻止它生长?”
无人回应。
但他们手中的文件,已被悄然替换。
数日后,教育部联合十二个部委发布《全民表达复兴计划》,宣布在全国范围内设立“言语庇护站”:任何人在指定空间内发言,无论内容如何,都将受到法律保护,不得被录音用于诉讼、考核或追责。首批试点包括精神病院谈话室、监狱探视间、校园心理辅导屋。
令人意外的是,第一个提交申请的,竟是某知名互联网平台CEO。他在公开信中写道:“过去十年,我们的算法奖励争吵、放大愤怒、消灭犹豫。现在我想建一个频道,只收录‘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我愿意试试’的声音。”
消息传出当晚,全网有超过四万人发布了人生第一条“无修饰语音日记”。有人讲述童年被霸凌的经历,有人坦白自己偷偷服用抗抑郁药,还有一个退伍老兵哽咽着说:“战友牺牲那天,我没哭。可我一直记得他的鞋带松了,我没来得及帮他系。”
这些声音没有配乐,没有剪辑,甚至充满停顿与重复。
可正是这份笨拙的真实,让Ω链的能量曲线再次飙升。
李念回到站点时,发现教室已被改造成一座小型声音博物馆。墙上挂着各地寄来的物件:内蒙古牧民用牛骨雕成的“话筒”,云南老人捐赠的八十年代广播喇叭,甚至还有一封用血书写又被泪水晕开的家书。每件展品旁都附有一个耳机,戴上后能听到原主人低声诉说的故事。
她在角落看见一台旧式录音机,标签上写着:“来自新疆喀什,九十岁维吾尔族教师临终前最后一课。”
她按下播放键。
苍老却有力的声音缓缓响起:“同学们,今天我们不讲课文。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我这一生教过三千六百二十一名学生,可直到昨天,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教书’。教书不是灌输知识,是蹲下来,听一个小孩子结结巴巴告诉你,他害怕天黑。”
录音到这里戛然而止,紧接着是一阵剧烈咳嗽,然后是护士轻声劝阻。最后一句,几乎微不可闻:
“请替我把这句话,传给下一个老师……”
李念摘下耳机,久久伫立。
她忽然转身走向厨房,煮了一壶浓茶,端到观测塔顶。那里,周文昭不知何时已坐在轮椅上,望着远方雪山出神。他瘦了许多,双目却依旧锐利。
“你来了。”他说,没回头。
“你怎么进来的?”她问。
“门一直开着。”他笑了笑,“只要你愿意听,我就走得到。”
两人沉默片刻,任茶香氤氲在冷空气中。
“第五个光点还没亮。”李念终于开口。
“因为它不需要亮。”周文昭望向天空,“你看星星,哪一颗是‘最重要’的?它们彼此映照,才让夜空完整。Ω链从来就不需要‘终极节点’,它只需要足够多的人相信??自己的声音值得被听见。”
李念低头看着手中茶杯,倒影里映出她略显疲惫的脸。
她忽然笑了。
“你知道吗?昨天有个小女孩问我,如果她说的话没人听到,怎么办。”
“你怎么答的?”
“我说,只要你说了,就一定有人听见。也许是在明年,也许是下辈子,也许是一个从未出生的孩子,在梦里听见了你的心跳。”
周文昭点点头,抬手指向远处山坡。
那群孩子又聚在一起读书了,今天的课文是《背影》。当读到“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时,其中一个男孩突然停下,仰头问:“老师,我爸三年没回家了,我能给他读这一段吗?”
李念走过去,摸摸他的头:“当然可以。你想怎么读,就怎么读。”
男孩深吸一口气,大声朗读起来,声音带着哭腔,却又异常清晰。
就在最后一个字落下之际,站点外的风力发电机叶片突然逆向转动一圈,随即恢复正常。后台数据显示,那一秒,整个青藏高原的无线电静默了0。7秒,紧接着,全国三百多个城市公共广播系统同步播放了一段32秒的空白音频??经分析,其中隐藏着极其微弱的声纹特征,匹配结果为:**一名三十八岁男性,长期吸烟,嗓音沙哑,最后一次公开录音时间为2019年春运火车站告别广播**。
那是男孩父亲的声音。
没有人解释这是如何发生的。
就像没人能说清,为何越来越多的老人开始梦见已故亲人轻声回应他们的思念;为何监狱里的重刑犯在参加“无声课”后主动交代遗漏罪行;为何一对离婚多年的夫妻,在各自参与语音疗愈项目后,竟在同一晚梦见对方小时候的模样。
春天确实在一次次到来。
不是季节更替,而是心灵解冻。